


2月25日,南海卫城墙遗址考古发掘成果暨东莞市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新闻发布会召开,会上介绍了南海卫城墙遗址考古发掘成果,认为本次考古发掘发现的明代南海卫城墙遗址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实证东莞作为“粤海第一门户”在明代军事海防体系的重要地位,证明东莞是“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节点,展现东莞建城史和城市发展史。


“揭示了明代海防卫城的空间格局与营建规制,是明清海防考古研究的重要成果。”“是东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节点的实物见证。”“清晰展现了东莞近千年的文化积淀和历史底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于2024年5月至12月对南海卫城墙遗址进行考古发掘,于2025年1月通过省文物局验收。>>详情

本次考古发掘了明洪武年间南海卫城墙和城内古建筑遗迹、遗物,是考察和研究明代广东军事海防体系、东莞县城建置沿革的重要实物资料,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位于东莞市历史城区莞城街道运河东二路与西正路交汇处,毗邻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迎恩门。
考古发掘面积3000平方米,最深处距地表约3米。


遗址内文化遗存丰富,现清理出的遗迹主要有城墙基址及道路、排水道等附属设施,城内房基、水井等生活设施。出土了明早期至民国时期的城墙砖、柱础、筒瓦、瓦当、滴水、铺地砖等建筑构件,以及陶器、瓷器、石器、骨器以及铜像、铜钱等日常用器残件。经初步整理,较完整、价值较大的各类小件360件,采集及出土的陶片、瓷片6000余片,可辨器型主要有盘、碗、杯、罐、盏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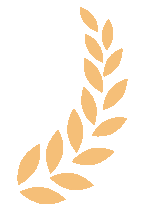
城墙基址整体保存状况较好,平面呈曲尺形,清理长度约100米。墙体宽约7.6米,内外两侧为红砂岩条石砌筑包边,中间包夹夯土,夯土残高约2米,层厚0.08米至0.12米,夯土层之间多夹杂贝壳或碎砖瓦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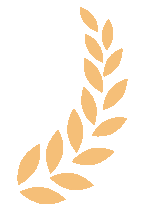
城内还清理出多处房址及水井等生活设施。其中房屋建筑基址6座,部分房屋以红砂岩条石为墙基,条石上砌筑青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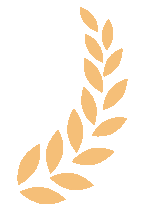
发现的文化层堆积从宋代一直持续到民国时期,最深处距现地表约3米。出土包括建筑材料及构件、其他器物。

在东莞“城市原点”莞城,人们熟知的西城楼北侧,“东莞记忆”项目原计划建设的迎恩门公园地块,发掘出明洪武年间南海卫城墙遗址,成为近年来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单次考古发掘面积最大的项目,填补了东莞古城遗址考古的空白,实证了东莞在古代广东海防体系及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地位。
走过600余年的风风雨雨,迎恩门的身旁,这片遗址“沧海遗珠”般乍现。一座千万人口的特大城市,为一处过往,定住眼眸。>>详情




1
据历代《东莞县志》记载,南海卫城墙于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由南海卫指挥使常懿兴建,明、清两代多次修缮和改建,而该段城墙毗邻迎恩门城门,其位置与文献记载的南海卫城基本相符,综合判断该段城墙应当为明代南海卫城墙。


南海卫是明朝实行卫所制的军事编制后在东莞县城设立的军事机构,与行政建置下的东莞县并存。作为明代广东海防体系"卫-所-寨"三级防御系统中的核心卫城,南海卫承担着广东中路海防体系中军事指挥中枢与海防前哨的双重职能,也体现东莞在拱卫广州、守卫祖国南疆、维护国家统治和沿海秩序的重要作用。其城防遗存的科学揭露,揭示了明代海防卫城的空间格局与营建规制,是明清海防考古研究的重要成果,对于研究明清海防史、建筑史、社会史等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2

遗址内出土奇石窑、龙泉窑、景德镇窑、建窑、白马窑等窑口的瓷器,深刻的反映了东莞是宋代至明清时期中国南方沿海地区内外贸易的重要中转站和集散地,是东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节点的实物见证,对于古代海陆交通史、贸易史的研究提供极大的丰富和补充。
3

本次考古发掘规模较大,收获丰富,填补了东莞古城遗址考古的空白,是岭南地区城市考古的重要收获。遗址内各类遗迹和遗物生动还原了东莞宋代至今生活场景,清晰展现了东莞近千年的文化积淀和历史底蕴,是东莞的文化地标,对于赓续东莞历史文脉、增强地域文化认同有着重要作用。

接下来,东莞将加大对南海卫城墙遗址的保护力度,高水平规划建设南海卫城墙考古遗址公园。南海卫城墙考古遗址公园面积约2.5公顷,在寸土寸金的莞城,这样的“留白”极其难得,又确切地值得。
依托考古遗址公园,东莞还将推进公众考古工作,提高公众对东莞历史文化的认知、对文物保护和考古工作的参与度,凝聚起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本土历史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